编者按:自《情满风则江——校友笔下的绍兴文理学院30年》征稿启事发布以来,校友们来稿踊跃,他们回望流金岁月,追忆青春故事,对母校的脉脉深情,像风则江一样,在笔端静静流淌。从今日起,开设“情满风则江”栏目,择优推送校友们佳作。欢迎校友们继续来稿,为风则江注入更多的温情与激情,激起更多校友的共鸣。
秋天,是一个多思的季节,让人想到收获,想到春播夏种。
秋天,又是一个多情的季节,让人怀念书声,怀念师恩,怀念同窗之谊。
当惠风越过漫长的暑热,穿越一条命名和畅的堂街、传递着秋凉的爽意之时,我听到了一声悠远的召唤。那一声召唤,别了“狂人”的泛黄的日记本,湿漉起曲尺柜台上发散着酒气的“茴”字,以和畅堂的秋风之吟,拖了长调,牵引出一个青年的文学梦,步入明净的课堂,聆听净化心灵的教义。
从解放路口,到风则江畔,打捞一条叫和畅堂的老街的记忆,仰望汉语言的璀璨星光,最好的支点是秋瑾故居的台门口。
向东是解放路口。无数次,一个清瘦的身影在路口张望,目光中满含向往,失落于1988年夏日的黯然分流。从此,我的同学十余人坐在了风则江边明亮的教室,每一次探望,与我隔了一道无形的栅栏。他们中许多人报了中文系,而我这个文科班的语文课代表再也无缘手执教鞭走上讲台,成为一名语文教师。若干年后,我的高中同学胡奇良送给了我一个惊喜,把他在绍兴师专就读的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共5册递到我的手上。此刻无须太多的言语,我们彼此最懂对方的心意。
西望是宽阔的风则江水,流淌着龙山千年的文脉、西园的诗会吟诵,留下鲁迅从绍郡中西学堂下值后腋下挟着讲义匆匆行走的矍铄身影。南望是山阴道上俯仰天地、品类万物的魏晋遗风,直抵永和九年的那场传颂千年的兰亭雅集。一个被丰饶的地域文华浸泡着的年轻的灵魂,不知何年,已植入了一个如茧丝般修长而坚韧的文学梦,拾起了清贫而饱满的文苑逐梦之路。
2002年,在工作十余年后,我终于迁居城里。最大的便利是,我可以就近入学,去实现我那接受中文系高等教育的心愿。
我迈开坚定的步伐走进和畅堂老街,去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绍兴分校找我初三时的语文老师徐越舫。徐老师其时已从乡村中学调到绍兴电大的教务处工作。见面后,少不了寒喧几句。之后,我们的思绪便回到1984年秋天,那是激发一个少年追梦文学的美好时光,那年我荣获了“六乡镇作文竞赛一等奖”,以至于我与徐老师多年之后的这次晤面,满是欣喜的回忆。我说明了来意,想要攻读汉语言文学专科,她领我去见了后来的班主任老师王尧根。随后,我便成为电大秋季班的学员,坐在了风则江边的明净教室里,坐在了叫不出名姓的学长学姐们坐过的桌椅前,听中西方的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文鉴等专业课程,听普通逻辑学、中国革命史、法学等选修课程。也许,我身边的同学所念的大都是一张学信网电子注册的大专文凭,而我不同。我的职业是会计,但我割舍不下炽烈的文学情怀,毅然报读了汉语言专业,只为开拓文学的视野,延续我的文学梦。
两年的面授很快结束。而我的文学梦真正得以拓展的,却是2008年秋天的一则E网公告——越城区文联计划筹建文学爱好者协会,招募区内的文学爱好者成为首批会员。
我以“香林文学社”成员的身份,以及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作品的简历,受到了重视,加入了筹备组,成为了副会长。此后,我与协会共成长,在组稿、编辑《山阴》杂志的同时,个人先后成为绍兴市作协、浙江省作协会员。其时,我已担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,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。在我的提议下,越城区文学爱好者协会改组为越城区作家协会,并申请成为绍兴市作家协会的团体会员。
当我加入到更高一级作家协会的时候,给我提供方便的是,可以参加一些由省、市作协主办的培训讲座、笔会、改稿会,听名家现场介绍文学创作经验。与此同时,我的创作文体也慢慢地由散文转向现代诗,最后把着力点落在了纯文学小说的创作上。
2015年3月,于我而言是一个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间点,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了《野草》杂志当年第2期。从此,我的创作空间彻底打开,先后在二十多家刊物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出版小说集、诗集,荣获中国作协《文艺报》、中国诗歌学会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颁发的奖项多次,并于2023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
回顾我的文学追梦路,我经历了从早期的“原生”创作到2015至2024年期间的“规训”创作两个阶段。所谓“原生创作”,即凭着个人对文学的初浅理解,质朴而无序地生产文学作品,满足于地方报纸的“熟人读者”的传播度,缺乏视野,游离于主流文学圈以外的自娱式写作。所谓“规训创作”,则是在官方主办的文学讲座、笔会、改稿会的名家思维指导下,以及杂志编辑用稿的规则辅导下,展开符合主流媒体用稿的“口径化”创作。
2025年年初以来,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创作中的视野问题:每一种写作都在书写原生的地域文化,而“地域书写”往往会落入到“民族的便是世界”的这一自恋式命题窠臼,期间是否掩盖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异?本民族的“地域书写”文本对世界文化的传播是否具有先进性?落后的“地域书写”是否存在夜郎式的“洞穴狂欢”?
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作品脱不下“翻译腔”这件“洋马甲”的“口吃”小事了,而是离现代文明有多远的“肌理要务”。由此,我发现自己的创作默默地转入到了“求索”阶段,即,先别急着写,更不要盲目地批量生产,尤其是尽量避免消耗素材的无效写作。
这样说很容易引来不同意见,甚至争议。那好吧,我们把个人创作历程的话题收回来,说说我与母校的文学互动。
2021年6月,我在市作协群看到了一则校友诗歌征文活动的消息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拟了一组现代诗《和畅,一抹红色的飞白》,发送给指定的邮箱。之所以忐忑,是由于不确定我作为一个绍兴电大的学员能否被列入校友范围。所幸的是,我的组诗后来荣获了“双十佳”奖项。6月20日,我还应邀参加了“校友诗社”的成立大会,在合影时战战兢兢地站在了不显眼的后排。2024年1月20日,我受到了校友会的邀请,参加了当年的迎春晚会。在参加校友活动时,我最怕被问及的是:你是哪一届毕业的?每每于此,我会面呈愧色。我是电大生,不是校友眼神中“希望”的本部生,很难无障碍地给予回复。有一次,我很不自信地回复:我是2002届中文的。马上引来对方的惊讶:从面相上看你年纪比我大,原来却是我学弟!我怯怯地说:也许是我这个人长得有点着急吧。
自然,这篇文字从第一个读者看到时,我就成了透明人了。这基于散文这种文体的写作特点,直面读者,藏不住心迹。诗歌是隐喻的精灵,小说表现生活的荒诞,两者可以隐藏起自己。
文学是一位可以对抗孤独、贪婪、自卑、浮躁的良师益友,勿忘初衷,相伴终生,你的人生虽说不一定会精彩纷呈,但却一定可以意趣盎然。
走过一条辛亥年的老街,是风则江畔逝水如斯的一声轻叹。秋水赋兴起一篇悠长的辞章,吟诵母校三十诞春秋的书香与辉煌。
作者简介:
王锦忠,男,1969年出生, 2004年电大中文。中国作协会员,绍兴市作协副主席。2008年2月注册绍兴金源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、绍兴会计信息网。在《传记文学》《飞天》《延河》《西湖》《文学港》《海燕》《都市》《野草》《泉州文学》等二十余家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文学作品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时光的飞白》、诗集《岁月拓片》。长篇小说获浙江省作协立项扶持,中篇小说获中国作协《文艺报》“光阴故事奖”,散文获评中国艺术研究院《传记文学》优秀作品,诗歌获中国诗歌学会“李白杯”优秀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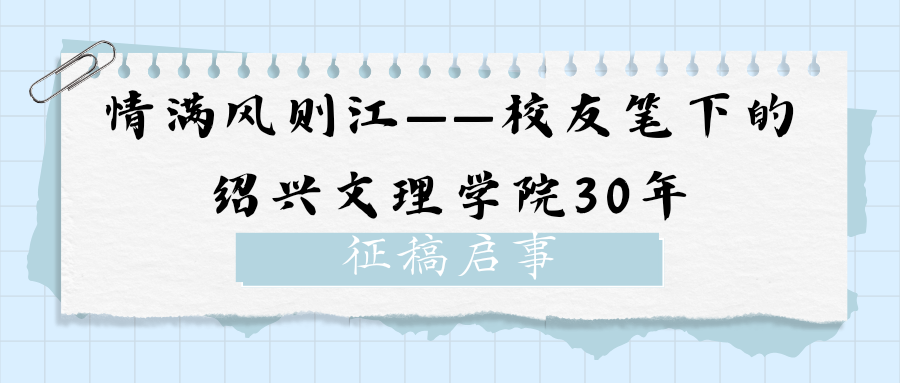
投稿方式
要求:电子文稿(word格式、小4、仿宋体、行间距20)
电子邮件发至:100@usx.edu.cn,并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“情满风则江”字样。






